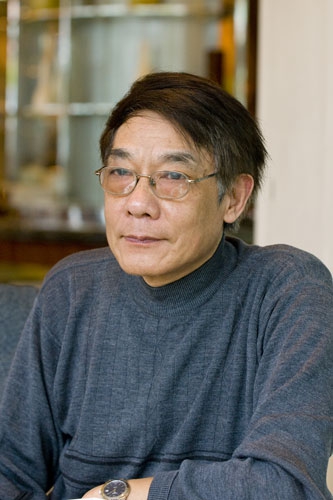
陈淳:
复旦文博物系教授、博导,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著作有《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考古学理论》和《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等。
人类对自己的来历天然有一种好奇心和探索的动力。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最初人们都普遍认为,对人类历史的了解只能来自于文字的记载。即便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100年,埃及的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中国的甲骨文出现在公元前1400年,但是直到公元前700年以后,无论在中东还是在中国,这些文字记载并没有提供详细的历史记载或对当时事件的分析性记叙,因此对于详细了解我们的过去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均变论、进化论与早期人类
18世纪是地质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诞生的时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居维叶提出了“灾变论”来解释地质和生物的历史。
1883年,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出版了三卷本《地质学原理》,奠定了均变论的基础。均变论否定了神创的灾变论,认为地球是由自然和持续相同的过程所创造。均变论成为进化论的基础。
达尔文和解剖学家赫胥黎在比较了人类和现代类人猿的骨骼之后,认为我们与非洲猿类最为接近,因此推测人类的起源地可能在非洲。但是和达尔文同时创立了进化论的华莱士则认为亚洲是人类的摇篮。1892年,荷兰解剖学家杜布哇宣布在印尼爪哇的特里尼尔发现了一个远古人类的头盖骨和一根股骨,认为这就是人类的远祖,是他苦苦寻找的人猿过渡的“达尔文缺环”,并将它称为“直立猿人”。但是,这一发现受到了普遍的质疑。
20世纪初大部分古人类学家认为亚洲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对亚洲地区的重视,使得受聘于中国政府的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开始在中国寻找远古人类的证据。1921年,安特生找到了周口店的龙骨山遗址。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1929年发现了第一个中国猿人的头骨化石。中国猿人化石的发现拯救了爪哇人,确立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论。结合爪哇人和中国猿人的材料,学界确立了人类起源的进化理论,亚洲自然被看作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1924年,南非解剖学家雷蒙德·达特发现了一件被称为“塔昂幼儿”的灵长类头骨,称其为“南方古猿”。
1932年,美国古人类学家刘易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发现了一件中新世晚期的灵长类化石,称其为“拉玛古猿”,认为它是人类最早的祖先,其生存时代约距今1400万年前。直到20世纪70年代,拉玛古猿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早远祖的代表,亚洲自然也成为人类起源的一个中心地区。但是,后来出土的大量化石证明,拉玛古猿是现在亚洲猩猩的祖先,它和另一类总是同时出土的西瓦古猿是两性区别。于是,拉玛古猿被归入西瓦古猿的分类名称之中。
20世纪中叶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和玛丽·利基夫妇于1959年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找到了一具几近完整的灵长类头骨,称为鲍氏东非人。后来几年中,在附近又发现了“能人”,并认为这个地点的石器应该是能人制作的。鲍氏东非人被改名为南方古猿鲍氏种,能人才是人属的最早代表,钾氩法测定的年龄为距今175万年。
自20世纪中叶开始,从南非和东非出土了大量南方古猿和人属的化石,特别是最近两年在东非发现了许多400到700万年之间的人科化石,为人类的非洲起源说提供了充分而有力的证据。同时,拉玛古猿作为最早人类远祖的地位也因新证据的积累而被否定。
起源何时?祖先是谁?
测年技术对于考古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丹麦学者克里斯蒂安·汤姆森提出了以石、铜、铁三个技术演进序列为基础的三期论,作为对物质遗存进行相对断代的方法,被公认为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标志。于是类型学和地层学成为考古学家解决文物年代的主要方法。1949年,化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了碳14绝对测年方法,成为考古学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利比因此获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
该测年方法的诞生对考古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为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年代学标准;这一方法将考古学家的精力从类型学的断代工作中解放出来,能够关注和探索其他更重要的历史问题。之后,大量其他各种物理和化学的测年法被发明和用来进行断代,比如钾氩法、铀系法、古地磁等。
由于周口店猿人已经制作工具和用火,应该是真正的人类了。于是,猿人这个称呼逐渐废弃不用,开始称其为“直立人”,简称北京人。根据年代测定,北京人大约生活在距今60~40万年前。
20世纪60年代,钾氩法对奥杜威地点的年代测定,将人类起源的时间至少延长了两倍。学界一般以制作工具为真人的标志,因此与石器共生的能人被归入人属。而这一时期人类学家古多尔对黑猿的长期研究后,认为黑猩猩具有许多原来被认为是人类特有的行为特点,包括使用工具,人类学家们开始相信两足行走应该是人猿分化之后最重要的变化,因此他们从直立行走的确立来追溯人类的先祖。
同时,遗传学家开始采取一种革命性的方法——分子钟来确定人猿分离的时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萨利奇和威尔逊在比较了人、猿和猴血清白蛋白之后推算,人和猿大概是在500万年前分道扬镳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DNA技术的改进已经能够更加精确地推断人和猿的亲缘关系,这一方法表明人和黑猩猩的关系最为接近,并且推算出人与黑猩猩分手的时间大约在800~500万年之间。然而,当时这个根据遗传变异速率推定的时间,尚未得到化石证据的支持。
1974年,美国古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在埃塞比亚北部的哈达地区发现了一具320万年前的南猿骨架,取名为“露西”。1975年,约翰逊团队在另一个地点找到了更多的化石,大约代表了和露西相同的13个个体,于是他们将这类早期人科命名为“南猿阿法种”。虽然露茜还不会制作工具,但是阿法种被认为是人类演化谱系上最早的成员。1978年,玛丽·利基在奥杜威峡谷的莱托利地点发现了南猿阿法种在火山灰上留下的脚印,从脚印判断阿法种身高约1.2~1.5米,已经能够完全直立行走,这些脚印可以用钾氩法对火山灰直接测年,得出了距今370万年的结果。
1994~1995年,伯克利分校的怀特在埃塞俄比亚阿瓦什中部地区出土了阿法种更加原始的材料,将其命名为一种新属新种“地猿始祖种”,它们的生存年代为距今440万年。怀特团队后来在这一地区又找到了更早的材料,达580万年,命名为地猿始祖种家族祖先种。
地猿的先祖地位刚确立,一支由法国和肯尼亚的联合研究小组公布了他们在肯尼亚图根山区发现的12件化石,这批绰号叫“千僖人”的材料被发现者认为是一种前所未知的属种,年代测定在620~560万年之前。
2001年在乍得丢拉伯沙漠中又惊现一具头骨、一个下颌骨和一些牙齿。这批新材料被命名为撒海尔人乍得种,绰号“托麦人”,年代距今700万年,很可能是人科演化主线上的早期代表。
怎样进化?
长期以来,我们以一种单线直进的模式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演化。20世纪50年代,学界将人类进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猿人、古人和新人。在南方古猿发现后,学界建立了四阶段的进化模式: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
随着化石材料的积累,古人类学家们发现人类起源和演进的轨迹非常复杂,完全不是以前所想象的那种单线直进或阶梯状递进,更像是错综复杂的树丛甚至藤蔓。到上世纪中叶,东非和南非出土了大量的南猿化石,学界将它们归入两大类:一类是南猿非洲种或纤细种;另一类是南猿粗壮种。
到上世纪90年代,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已经达1000多个个体,命名了8个种著名古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将人类的进化谱系称为“一个拥挤的人科”。如何解释这些人科化石与人类之间的演化谱系关系,成为学界讨论的焦点。
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各类物种都有许多亚种或变种,包括人类的近亲猿类也有至少四个物种,现在看来人类的演化过程也不例外。这一过程是和其他物种类似的成功与失败的尝试,它完全不是过去想象的那种新旧更替的累进,而更像是竞争激烈的淘汰赛,最后只有一个成功者胜出。早期的竞争者很多,在我们进化谱系上最后一个被淘汰的是尼人。
最近《自然》杂志报道,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发现了一支未知的古人类。这项发现之所以惊人,是该项发现不是根据以往骨骼化石的形态分析,而是首次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线粒体DNA序列鉴定的一支新人种。
从人类的进化来看,其演化速率看来不是一种缓慢均变,而是一种间断平衡。间断平衡是一种生物学理论,认为生物进化并非像达尔文所想象的是一种持续的渐进,而是长期所处的静止或稳定状态被突然或爆发性的进化所打破,出现许多新的物种。这一理论也能用来解释人类进化的现象。
尽管人类演化的细节尚不清楚,但是总体趋势大致如下:首先,大约在600万年前人猿分化,关键的转变是直立行走。第二,大约在250万年前人类开始制造石器,真正的人属诞生。第三,大约在200~100万年之前人类脑量迅速增加。最后大约在20万年前现代人种出现,开始利用强大的思维器官逐渐创造出艺术、音乐、语言和其他文化特征。
人类历史与学科交叉
文科与理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向来被看作是泾渭分明的学术分野,高等教育长期来也遵循着这条路径。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文理结合与学科交叉显示出日益加强的趋势,人文科学凭借自然科学的高新技术,对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认识,而自然科学手段将人文科学中的难题看作是自己新的探索领域,使得科技手段有了更加广阔的施展空间,在这一方面,考古学是非常典型的一个领域。考古学是了解人类的历史,但是它自诞生开始,就努力超脱文献研究的窠臼,依赖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解决自身的问题。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学的手段越来越依赖自然科学的方法。一些自然科学的新兴领域正是在考古学领域大显身手,才凸现非凡的潜力和发展前景,其中化学的放射性元素断代和遗传学和分子人类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面对大量信息的提炼和积累,考古学家则从其他社会人文科学,如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和哲学领域借鉴相关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模式来解释这些信息中所蕴含的人类行为意义。
在欧美,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完成了文化编年学向科学考古学的转型,从编年史的附庸转向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与国家起源等战略性课题的探究,并成为全球考古研究的基石。这种研究也从历史事件的记载转向探究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原因,说明人类社会如何及为何发展,这些经验对当今的社会决策有何借鉴意义。
在这一研究取向的激励下,各种科技手段蓬勃发展起来,运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地学,涉及地质学和土壤学的环境研究;植物学,涉及利用植物、孢粉、植硅石、树木年轮对生态气候的重建;动物学,涉及哺乳动物、鱼类、贝类、昆虫等生物链的重建;人类,涉及墓葬、病理学、食谱和遗传学的研究;器物和原料,涉及石、陶瓷和金属等工具的生产和使用。
文物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采用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技术、等离子发射光谱法和粒子诱发X射线荧光分析(PIXE)都是一些无损伤的探测技术,可分析少量陶瓷样本中的痕量元素。
微痕分析来了解石器的使用痕迹、骨骼上的工具切痕或动物齿痕,以了解工具如何使用,以及人类对肉食的利用。
在社会人文科学方面,许多社会科学理论和阐释模式也和考古学进行频繁的交叉,比如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的功能论、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理论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民族学家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以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等都被考古学家用来构建考古材料中人类行为动态阐释的模式,考古学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大熔炉。
结语
目前,考古学科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对方法问题的日益关注,并对早期研究结论的怀疑。在研究技术上,则越来越多地从自然科学中引进方法和技术,并在研究分析上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而在材料的解读和阐释上越来越多地结合社会人文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考古学术圈里,人文科学已经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建立起更为稳固和融洽的联系。考古学的实践更像科学研究,需要像其他自然科学专家一样收集材料和证据,做实验,构建假设用来解释材料,并用更多的材料予以检验,从而提出一种最佳陈述。考古学家的历史重建也是通过相同的途径才能取得,这种历史图像并不能现成地从材料中自动显现出来。
以当今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为例,一些人文学科不仅需要不断增加和改善本学科的技术和方法,而且需要熟悉和掌握那些看起来与自己研究领域毫不相干的科技方法,而且专业化和分工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对于这种学科交叉的趋势,需要从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并列,转向跨学科研究一体化的协调与合作。后者才是科学考古学的最终目标。
法国学者皮埃尔·德·拜勾画了多学科交叉的一种渐进过程。以考古学为例,早期的学科交叉,考古学家常常会将其他领域科技专家的工作看作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低水平的交叉研究阶段,考古学家求助于“辅助”学科,向其他学科专家索求一些资料和帮助,这些科技专家并不关心考古学科,而是提供测定、化验和提供分析的帮助。到第二个阶段,科技专家作为合作伙伴介入到研究中来,但是一种分担任务的角色,解决考古学中的某些问题。第三个阶段,就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共同承担任务,提出问题,制定研究方案,并全方位来探索人类历史的进程。这时,科技专家已经不是辅助人员,而是和考古学家一样的主导研究的决策者和研究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进行农业起源研究时,就是以这样的团队展开工作的,野外调查发掘除考古学家外,还包括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土壤学家,此外还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参与年代测定和文物的实验室分析工作。
最近几十年,见证了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与此同时,研究材料也越来越广,种类也越来越繁杂。这使得考古学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发掘比原来更为缓慢,这样才不会遗失和疏漏土壤中包含的任何材料和信息。二是我们可以从每件器物上获得更多的信息。
回顾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理性思维在科学发展中是极其重要的。现代科学思想将世界看作是一种自然和独立存在的客体,通过抽象思维和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方法,能够将经验观察变成洞悉与解释真实世界的科学理论。